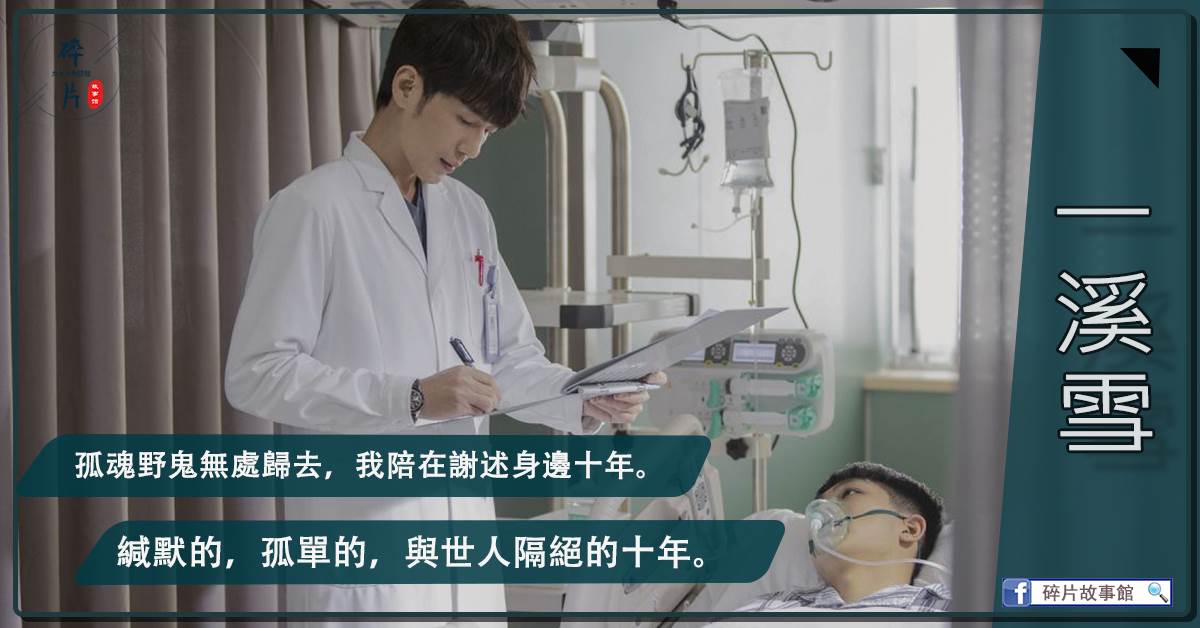《一溪雪》第5章
「周樹最近冷落了你了是吧?」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程茹被我戳中,動作一滯。
開口要問:「你——」
「因為他和簡秋煙在一起了。」
「程茹。」
「你知不知道——」
「每天放學,他們都會去舊器材室約會。」
「簡秋煙說你好蠢呢,他們在一起快一個月了你都沒有發現,還傻傻地約著周樹去看電影。」
「程茹,你怎麼不僅倒貼,還被人耍著玩呢?」
「你他媽放屁!」程茹暴跳如雷。
「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笑:「信不信隨你,他們現在可能在一邊親嘴一邊笑你吧。」
「你他媽——」
程茹拿了棍子想打我,卻又堪堪停住。
「陳絮,他們今天要是沒在那里,你以后就完了。」
撂下狠話,她轉身就走,步伐急促。
等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拐角。
我低下頭,攤開掌心握緊的鑰匙——
舊器材室大門的鑰匙。
不會有以后了。
程茹。
18
我沒有騙他。
上輩子,周樹和簡秋煙愛在那里深入交流。
我們學校很大,舊器材室在校園最角落。
那邊有一片小林子,還沒有監控,基本沒什麼人過去。
只有管理的老爺爺,每天會去開門關門。
老爺爺記性不太好,弄丟過好幾次鑰匙,偶爾會忘記關門。
上輩子器材室曾經發過一場大火,把建筑燒成了一具空殼。
只有我知道,是周樹做的。
他喜歡抽煙,和簡秋煙一塊兒時疏忽大意,火燒起來之后他卻逃了。
還威脅我不準說出去。
學校找不到人,也就不了了之。
程茹走后,我馬上跟了上去。
路上的人很多,越往那邊走人越少。
穿過樓棟時,身后卻有細碎的窸窣聲,我回頭卻不見任何人。
上輩子直到大火燃盡,他們才發現失火。
說明這邊根本沒有人來。
我壓下心頭的一點疑慮。
19
器材室的門輕掩著,里面的人說話聲音,卻一點不差地傳出來:
「簡秋煙你這個賤婊子——」
「你他媽怎麼這麼賤啊!?跟他媽蕩婦一樣,脫光了被人——」
程茹的聲音戛然而止。
我站在外邊往門縫里看。
簡秋煙的衣服還沒穿好,被程茹揪著頭發用力往后扯。
周樹試圖去攔程茹。
程茹手里拿著一個鐵拍子亂揮,周樹躲閃,恰好撞倒身后的鐵架子。
放滿雜物的架子晃了晃,開始傾斜。
周樹嘗試去扶住,卻架不住。
他想喊人來幫他,卻沒有一個人聽進去了。
誰也沒有注意到,角落里的煙頭,已經點燃了最近的墊子。
我扯開嘴角。
輕輕把鎖拉上,鑰匙旋轉兩圈。
然后退后幾步。
館里傳來一聲轟響,還夾雜著周樹痛苦的嚎叫。
爭吵聲須臾被按下暫停鍵。
「周樹!周樹?你沒事吧?」
「等一下,等我們把這個架子抬起來。」
「簡秋煙!你這賤人!不過來搬架子還在穿衣服!」
又是一陣皮肉相碰的聲音。
然后是簡秋煙的尖叫:「火!火!火!」
「滅不掉!」
「放開我!我要出去!我找人過來救他!」
「你他媽放手!火越來越大了!」
簡秋煙的聲音靠近大門,門發出重響,一下又一下。
伴著她絕望的吼聲:「門打不開了!——」
「他媽的!有人嗎!救救我!」
聲音混亂成一片。
有煙從窗戶飄出來。
我站在原地。
尖叫聲,怒罵聲,哭聲,撞門的聲音。
像是地獄魔鬼的邀請。
我沒有動,只是看著。
程茹的聲音很尖。
從怒罵,到哭喊,再到祈求。
ADVERTISEMENT
就像上輩子那樣。
我想再笑得開心些。
只是嘴角像是僵住了。
眼淚在我沒有意識的時候落了下來。
笑著笑著哭了。
哭著哭著又笑了。
困擾我兩輩子的噩夢,好像就在這樣絕望的哭喊中,慢慢消散。
20
我轉身,想從小林子的另一邊走掉。
風吹起地上的落葉,帶起了一兩片。
我抬頭時,卻看見了一個最不該出現在這里的人。
謝述。風吹起他額角的發。
謝述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目光從我臉上,移到身后冒著煙的器材室。
我怔住。
21
謝述是個純粹的好人。
他寡言,冷淡,外表像是經年不化的高原雪。
內里卻是如春般的溫柔。
像是無瑕的白玉。
溫良恭儉讓。
他有光明的前途,有大把的人脈,還有會偷偷看著他臉紅的小姑娘。
曾經新來的小護士很漂亮,齊劉海,鵝蛋臉,一見他就臉蛋紅撲撲的。
科室的人愛撮合他們。
偶爾小護士拿了自己親手做的小餅干送給謝述。
周圍人起哄,我也在旁邊看著。
小護士真的很漂亮。
可謝述卻沒有接。
他道了歉,疏離地拒絕。
小姑娘紅著眼走掉。
朋友調侃他要孤獨終老,他卻什麼也沒說。
如果他接受了呢?
如果他娶了一個相愛的妻子,如果他繼續做醫生,治病救人——
他或許可以很幸福地過完這一輩子。
可他沒有。
他違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違背了職業道德,違背了自己的天性——
他用手術刀,一片一片剜下霸凌者的肉。
卻只是問了他們一句:
「后悔嗎?」
我甚至不敢想,這十年他是怎樣走過來的。
也不敢想,這個計劃,到底是從什麼時候出現在他腦海里的。
他用刀,分開了自己和那個光明的未來。
一步步走向地獄。
靈魂是不會感到疼痛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