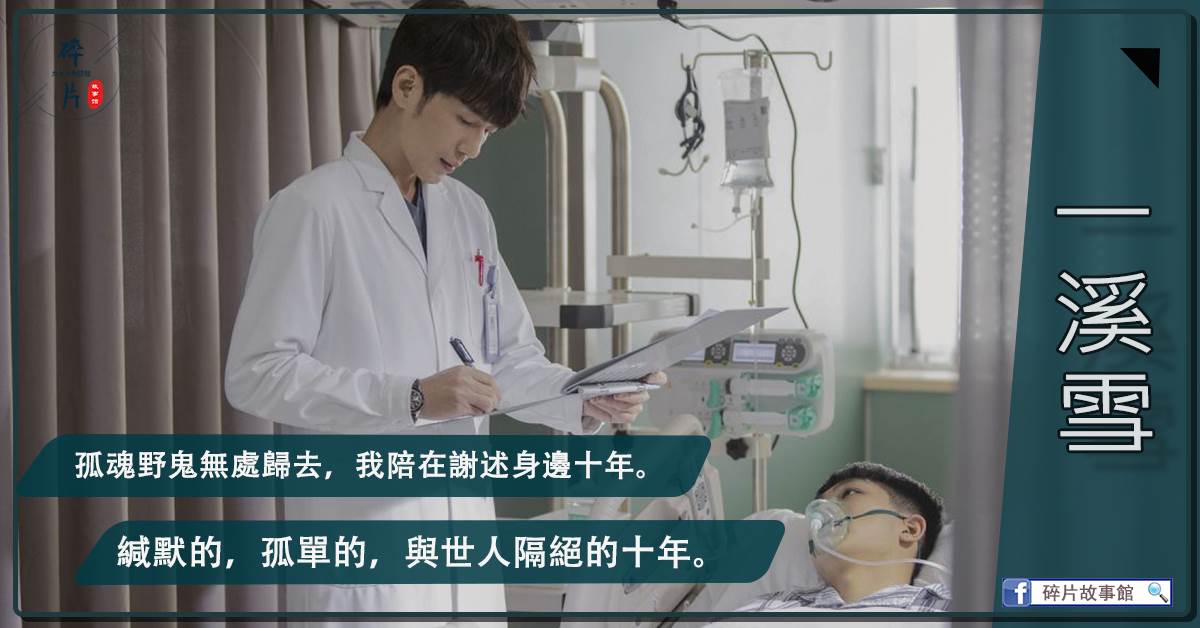《一溪雪》第7章
程茹他們沒有死。
只是這輩子和死了也沒有分別了。
周樹的腿被壓斷,又被高溫的鐵架子炙烤,下半輩子再也不能站起來了。
簡秋煙的身上有很多燙傷,需要做手術植皮,臉上也被燒傷了。
至于程茹——
她瘋了。
她曾經的朋友大肆編排,將她現在的情況如同笑料一般,眉飛色舞地講給每個人聽。
「她真的瘋了。」
「他們家把她關進瘋人院里去了,因為她不是一般的瘋,不僅攻擊自己還攻擊別人。」
「拿著刀就往自己身上切,像削肉片一樣,一片片切自己的肉。」
「邊切還邊哭『好疼啊,我錯了,我錯了別殺我。』」
她邊說著邊表演起來。
旁邊的人睜大眼睛。
「真的。」
「我那天去他們家,程茹就拿著刀砍自己,他爸媽攔她,她就對著她爸媽砍。」
「特別可怕。」
她說著,瑟縮了一下:
「誒我還聽說,是因為程茹喜歡周樹,但周樹喜歡簡秋煙所以程茹才想帶……」
我沒有聽下去。
起身出班級時,謝述已經在等我了。
他拉著我的手,一起往家走。
路上車流很急。
小販的叫賣聲,車輛的鳴笛聲,街邊人的閑聊聲。
吵吵嚷嚷。
我卻什麼也聽不進去。
一直到回了家。
門被關上的瞬間。
情緒如摧枯拉朽。
所到之處,盡數崩塌。
禁錮我的東西像是在那一瞬間消失了。
我跪坐在地上,終于放聲大哭。
25
如果世上真的有報應。
或許程茹他們所遭受的一切就能印證。
上輩子的周樹,愛用腿狠狠地踢我的腹部。
簡秋煙曾經用小刀在我臉上留下過劃痕。
程茹那長達一年的肉體和精神折磨。
一個不差地,還到他們自己身上了。
26
我哭到不能自己,像是要把十年來的所有苦痛,全部宣泄出來。
謝述跪坐在地上,將我攬進他的懷里,用力地,像是要將我嵌進他的身體里。
「沒事了絮絮。」
「沒事了。」
「都是他們的錯。」
「都是他們的錯。」
他的聲音有些顫抖。
像是極大的喜悅和極大的悲慟雜糅,呈現一種近乎瘋狂的情緒。
我忽然意識到了什麼,用手把他推開。
眼淚模糊了眼前的一切,我甚至看不清他的臉。
可我就是覺得有什麼不一樣了。
我想擦掉自己的眼淚,可是手抖了又抖。
面前的人伸了手,輕輕地拭去我眼角的淚。
視角一點一點清晰起來。
我對上眼前人的雙眼。
他的眼睛里面,倒映出一個小小的我。
狼狽的,痛苦的,卻又真真實實活著的我。
連著他眸子里萬千的哀戚。
還有失而復得的慶幸。
27
是我的謝述。
在漫長的時間里,無數次救我于水火的謝述。
我們——
終于再次相遇。
后記 1:陌上春
1
謝述患有分離焦慮和失眠。
他的失眠,從上輩子開始就很嚴重。
要到夜半才能睡著,即使睡了,也并不安穩。
他睡覺的時候,我就飄在半空中看他。
看他蹙起的眉,緊繃的下頜線,還有手邊的舊布娃娃。
是他小時候用零花錢給我買的。
我很早就嘗試過去撫他眉心。
可是沒有實體的手,只能消散在我即將觸碰到他的一瞬間。
偶爾謝述也會驚醒。
窗外的世界一片寂靜,只有月光落進屋里。
他不會開燈。
只是一個人靠在床頭,看著滿室銀白的月光。
ADVERTISEMENT
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我有時候覺得,謝述像個脆弱的玻璃娃娃。
在每個獨處的夜晚被摔得支離破碎。
碎片滿地都是。
我想一片片撿起,一片片將他修復好。
可我碰不到他。
拯救的欲望和現實的落差像磨石,將我反復輾軋。
在死后的第六年。
我終于放棄了再見他的念頭。
2
分離焦慮是謝述這輩子患上的。
具體表現在,他去往大學后每天一次的來電。
宿舍的公用座機,每天晚上總有一通他的固定來電。
打過來也不會說什麼要緊的事情,無非是:「今天過得怎麼樣」「今天的目標完成了嗎」「有沒有好好吃飯」……
也并不耽誤我的時間,兩三分鐘就結束。
謝述是個很克制的人。
他擅長于隱藏自己的心思,暴露在我面前的,永遠只有他溫馴有禮的一面。
某天周四晚自習下課回寢。
謝述的電話照樣打來,如例行公事一般問了平常的問題。
我隨口回答,對話陷入短暫的沉默。
新換的室友在喊我:「絮絮!我媽今天送了燒烤來,快快準備開吃了。」
高三的學習量驟增,與之對應的,還有胃容量。
晚自習后加餐,在我們宿舍再正常不過了。
謝述好像聽見了喊我的聲音。
「那我先……」
「謝述。」
我喊了一聲他的名字。
「嗯。」
「我今天也很想你。」
那邊的時間像是忽然停滯了一般。
好半天,我才聽見他的回答。
「我也是。」
「我很想你,絮絮。」
很想很想。
3
在我說完想他的第二天,謝述在周五下課后,坐了最近一趟火車趕了回來。
晚自習下課后,我走出教室,才發現那個熟悉的身影。
謝述站在走廊,在一群穿著校服的學生中間顯得格外突出。
我側頭對著室友指了指他:「我哥來找我了。」
室友了然,看清謝述的一瞬間,卻笑得有些意味深長:「去吧去吧。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