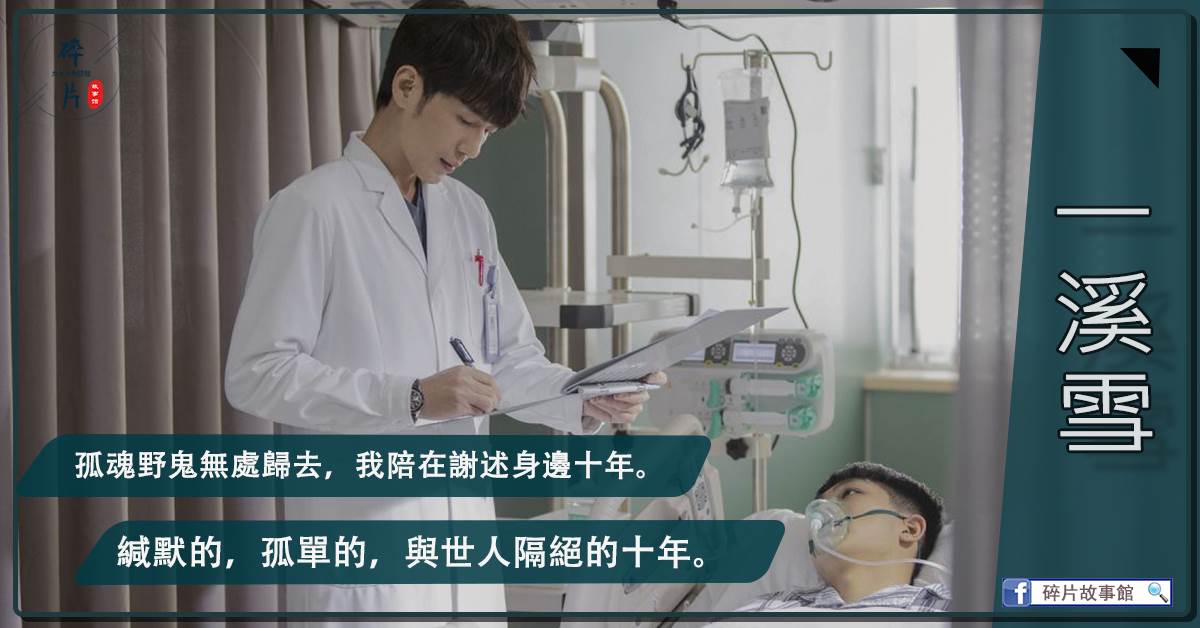《一溪雪》第8章
」
「謝述!」
「絮絮。」
謝述遞過來一袋東西。
我打開看了看,里面都是我愛吃的甜點。
宿舍關門還有半個小時,謝述陪我在小涼亭里坐了坐。
「怎麼突然回來了?」
小涼亭四周靜悄悄的。
我用勺子挑起一塊蛋糕,放進嘴里,唇邊沾了些奶油。
謝述拿了張紙,輕輕擦去我嘴角的一點,眸子彎了彎。
「想見你。」
奶油的甜香在嘴里化開。
我有些慌亂地又塞了一口,恰好又落了一塊在左手上。
謝述伸了手想幫我擦掉。
觸碰到我手的一瞬間,我快速收回,有些失措:
「我自己來。」
謝述不言,把紙巾遞給我。
我擦干凈后又用左手拖著蛋糕,放得低低的。
謝述垂眸。
「哥。」
「你再等等我。」
「好不好。」
「好。」
謝述答得很快。
我對上他的眼睛,里面有一片風平浪靜的海。
我的左手微微顫抖。
4
回宿舍時室友湊上來。
「那是謝述誒!」
「活的全校第一!!」
「絮絮你怎麼不早說他是你哥啊!」
「因為是一家人所以腦子都靈活是嗎嗚嗚嗚。」
另一個室友也湊上來。
哀嚎的瞬間卻忽然想起什麼:「不對,你們倆是兄妹,怎麼一個姓謝一個姓陳啊?」
「不是親的。」
我答到。
「有血緣關系嗎?」
「沒有。」
方琳眼前一亮:「是青梅竹馬!這麼帥你不打算發展些什麼嗎?近水樓臺先得月啊。」
兩輩子第一次有人和我談起這個話題。
我無端生出一種被人看穿的窘迫。
卻又隱隱地,覺得這似乎才是正常的高中生活。
我不曾體驗過的,和室友之間近乎于平常的打趣玩鬧。
如此普通。
又如此溫馨。
「你們住一塊嗎?」
「會有那種哥哥忘記帶換洗衣服,讓妹妹拿卻無意間春光乍泄的漫畫情節嗎?」
方琳扒著我不肯放手。
我覺得臉上好像有火在燒。
「……沒有。」
上輩子死后靈魂能任意穿墻。
謝述洗澡時,浴室的水汽一個勁兒往外涌。
我站在門外,看著倒映在玻璃門上人影,勾勒出男人漂亮的肌肉線條。
只感覺浴室里的熱水像是淋在我的身上一樣。
我試過邁出一只腳,手穿過門的瞬間,卻像是做賊心虛般又收了回來。
我像是想偷嘗貢品卻又沒有賊膽的小僧。
謝述是我心上佛。
我心惶惶。
不敢褻瀆半分。
方琳指著我的耳朵得意地竊笑,鬧著要去告訴另一個室友新發現。
我拖住她的的一只手,卻被她順道拖進懷里。
女孩子的懷抱軟軟的。
她抱著我笑,最后幾個人鬧作一團。
一切美好得不可思議。
此前種種,如鏡花水月。
亦或者。
是我幻夢一場。
5
謝述走時是周天。
回來的這周末我還在住校,每天留在教室里刷題,兩個人也沒有見幾面。
謝述本不想我送他,我堅持要去,給出的理由是總學著容易頭痛,偶爾也要休息半天。
送到火車站入口,謝述站定,回過頭看我。
混在嘈雜的人群里,我抬了頭微笑看他,剛想開口。
謝述卻伸了手,我沒反應過來,左手就被他扣住。
掌心相貼的一瞬間,我像觸電般想要扯回自己的手。
卻被謝述緊緊握住。
肌膚的每一寸被人緊緊裹住,包括每一處傷口,每一塊結痂。
「絮絮。」
謝述垂眸,和我四目相對。
我看見他眼里的海浪翻涌。
「不要傷害自己。」
我拙劣的偽裝和躲閃,被他毫不留情地揭穿。
ADVERTISEMENT
我在他眼睛里,再一次看見那個狼狽不堪的自己。
創傷哪有那麼容易好。
上輩子的傷口在漫長的時光里反反復復地疼,無處傾訴的痛苦和日復一日的折磨讓我潰爛生瘡。
肉體傷害是程茹對我施加的罪行。
卻在逐漸扭曲和殘缺的理性中,變成了我確認自己真實活著的唯一方法。
唯有疼痛,才能讓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還活著。
在拿著圓規向自己左手刺下去的一瞬間。
我像服下藥片的病人。
可同時我也清楚地知道。
我病了。
6
我不敢告訴謝述。
謝述也不想告訴我。
我們相互隱藏。
卻又都能輕而易舉地看穿對方。
我沒回答。
低下頭抵在謝述的心臟處。
聽他心臟跳動的聲音。
一下又一下。
他松了手,把我抱在懷里。
身邊人潮川流不息。
我們佇立其中,像兩個異類。
我沒有哭。
好半天,才從懷里抬起頭看他:
「謝述。」
他低下頭,湊近我。
「我不會傷害自己了。」
我會盡量克制住自己。
「嗯。」
謝述神色認真。
「我會監督你的。」
我看著他,認認真真描摹過他的眉眼。
「謝述。」
「嗯。」
「我忘了告訴你——」
「我也很愛你。」
從上輩子到這輩子。
一直都很愛很愛。
7
裹挾著恩情的愛太過沉重。
就像枷鎖。
可謝述從沒想要困住我。
他不曾提起,將自己框在一個合乎禮數的位置。
而我害怕傷疤暴露,總想著變好后再告訴他我的心意。
可是愛,本就是相互治愈。
我們都會好起來的。
后記 2:十年
謝述,男,2014 年于清園監獄去世。
生前患有 Maladaptive Daydreaming。
譯為強迫型幻想癥。
-完-
十四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