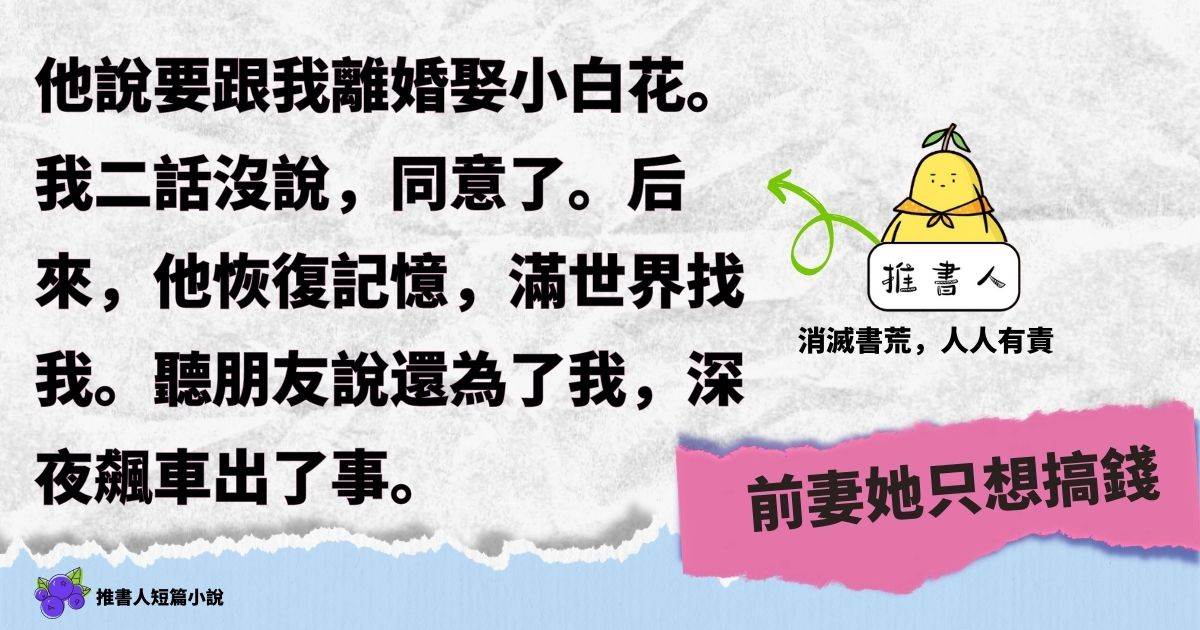《前妻她只想搞錢》第4章
」
我瞥了他一眼:「法盲?還是失憶把腦子也一起丟了?」
其實我很清楚,謝澤不是失憶把腦子一起丟了。
只是他沒有失憶前,被我們一起走過的十年道德綁架著,哪怕曾想過跟我離婚,也下不了那個決定。
現在失憶了,沒有了我們那十年的感情牽絆,或者說沒有了那十年我對他的恩情綁架,他可以肆無忌憚地做回他自己了。
他不慕強,他更享受林冉依賴于他,這能滿足他被需要的虛榮心。
用林冉來挑釁我時的話就是:「澤哥更愿意成為那道被追逐的光。」
果然,在我陰陽怪氣他后,他又道:「靜月,知道我為什麼第一眼就知道你不可能是我喜歡的人嗎?就是因為你強勢得讓人反感。」
我性格也確實很強勢。
但當初,謝澤明明說喜歡我這強勢的性格。
他說若不是我強勢地闖進了他的生活,他可能從大一開始,人就廢了。若不是我強勢的性格,在我們最初創業受阻他想放棄時,我拉著他站起來,我們也沒有今天。
我們結婚時,他望著我的眼里都還有光。
他說我是他一生的救贖。
如今,他失憶了。
我曾在他那里的萬丈光芒都開始刺眼了。
我扯了扯嘴角:「巧了不是,我也惡心你以前敢做不敢承認的慫樣。你也先別急著來我這里吠,把你送林冉的別墅還回來,離了婚,你愛怎麼給她買都是你的事。不然,我一定會將林冉告上法庭。」
謝澤還想說什麼,后腦勺突然被一只拖鞋給砸了。
他回頭,就見他媽手里拿著另一只拖鞋,撲過來對著他的臉又是一拖鞋:「靜月才引產完,你在這里狗叫什麼?」
謝澤:「……」
謝澤這才又朝我看過來:「你把孩子流掉了?」
我:「別說得你好像在意過一樣。」
但他真在意過,他在意有這個孩子,分財產的時候,他可能需要多支付我一筆贍養費。
謝媽更是警告過他,若一定要離婚,那就把公司他手里的股份分一半給孩子。
原本,我在公司就占股百分之三十五了。若因為這孩子,還要分他手里的股份,他的公司改姓無疑。
所以,我明顯看見他松了一口氣。
看,這才是他的本性。
而他竟然跟我演了十年情深,我都沒有看出來。
奧斯卡欠他一座小金人。
謝媽用拖鞋將謝澤打出去后,悲傷又心疼地看著我,想說什麼,最終什麼也沒說。
她是真的心疼。
我手術那天,原本沒跟她說的。
她不知從哪里知道了,我從手術室出來的時候,就見到她淚眼婆娑地在手術室外。見我出來,比我媽還先上前,拉著我的手,眼淚落得更兇了,泣不成聲:「閨女……」
我住院這十幾天,她近乎天天來看我。
我出院后,她親手給我做飯。
她說:「緣分盡了,也要好聚好散。」
但我知道,她自己也不好受。
謝澤為了林冉,跟她吵架時,在她心口插刀子了。
就是在她警告謝澤一定要離婚,讓他把公司的股份分一半給孩子時,謝澤跟她吼:「你連自己的兒子都不幫,難怪爸要跟你離婚。」
也是在那一瞬間,我突然就不愛謝澤了。
11
我又休養了半個月,才找謝澤談離婚的事。
這半個月里,謝澤除了那天回家里被我跟謝媽一起罵了一頓后,基本都在林冉那里。
ADVERTISEMENT
應該是謝澤重新許諾了林冉什麼,林冉雖然不爽,但還是把別墅跟這幾個月謝澤給她的錢還了回來。
我沒想到的是,謝澤在跟我談離婚協議的時候,竟然腦子有問題地希望我放棄公司的股份。
「車子房子存款全給你,但要斷就干干凈凈地斷,都離婚了,還同在一個公司,我怕冉冉誤會。」
他是絲毫不要逼臉,「所以,你放棄你手里的股份,離開公司。」
我:「?」
我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他,沉思了片刻點頭:「你說得對,不能讓林冉誤會了。所以,為了林冉不誤會,你凈身出戶。你都有愛情了,不能再在意這點股份、這點錢吧?」
謝澤:「公司是我一手做起來的,原本就跟你沒有關系。」
我呵呵:「你被車撞成腦殘了,不怪你,我給你提個醒,當初你發不出工資的時候,是我用我父母的錢幫忙發的。也是那時,我買了公司的股份。公司能到現在的規模,亦是我全程參與,出錢出力的。」
謝澤:「……」
我:「別賴賴唧唧地,讓林冉誤會你不想離婚就不好了。」
謝澤這時候不談林冉誤會不誤會了,咬死希望我放棄公司的股份,或者以最低價格賣給他。
是以,我們第一次離婚協議沒談妥。
我急。
醫生說謝澤的失憶是暫時性的,我怕再拖下來,婚還沒有離,他記憶恢復了,又想假裝自己是個人了,就更不好離了。
而離婚官司打起來耗時又長又麻煩。
于是,我一天三個電話地問候謝澤的同時,再給林冉施壓。
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讓人將我跟謝澤的過往剖析給她聽,又跟她分析謝澤萬一突然恢復記憶了,她想上位的計劃就要流產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