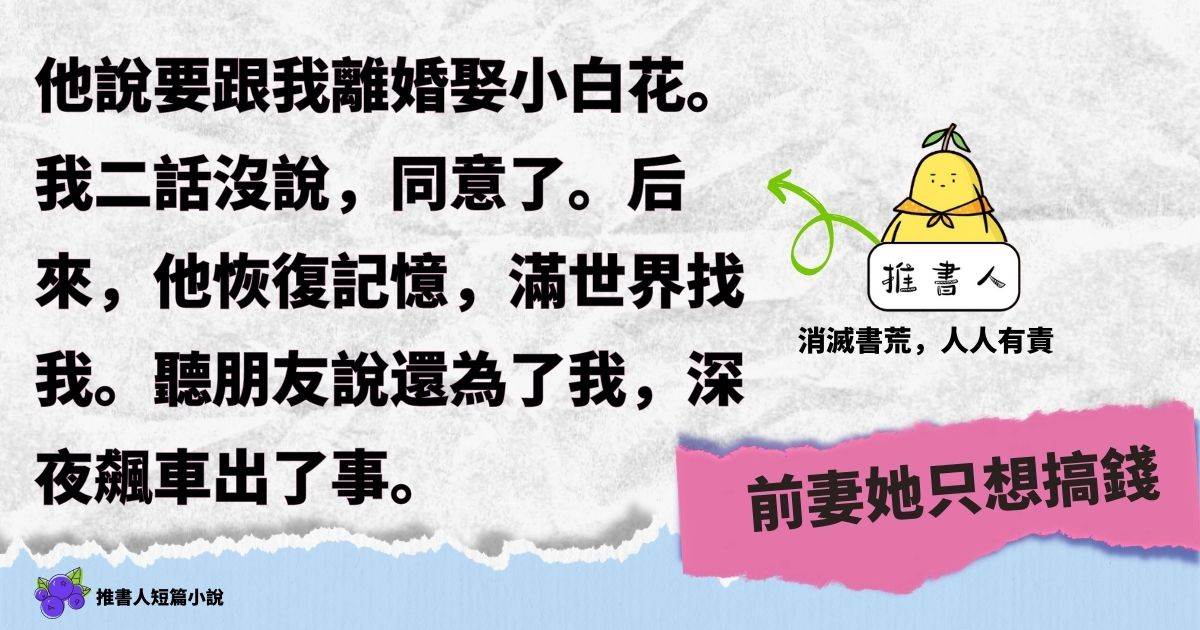《前妻她只想搞錢》第7章
而因著我跟謝澤離婚后,我放出的謝澤婚內出軌的消息,就已經影響了公司一部分合作。
自從我跟江城的公司開業后,為了慶賀我倆的新征程,我又把以前征途上的客戶也帶上了,又搶了謝氏不少單。
我承認,我就是故意的。謝澤既然只要真愛,應該不會在意錢。剛好,我在意,我只想搞錢。
所以,謝澤現在是公司家里都不安寧,不憔悴才怪。
林冉可不是當年的我,先不說她能力如何,現在的她懷孕生孩子的同時還要忙于婆媳大戰,根本幫不了謝澤在公司上的事,不添堵就不錯了。
當然,這不在我關心的范圍。
從謝澤為了林冉,往謝媽心口插刀子那一刻起,他在我心里,連個人都不算了。
但我快要路過謝澤身邊時,江城不知道哪根筋抽了,一把挽住了我的手臂,跟謝澤打招呼:「謝總。」
謝澤的眸子在我跟江城的手臂間多停留了幾秒。神色變化了幾次,最終淡然地跟江城碰杯。
事后,我罵江城:「你腦子出問題了?」
江城:「月月姐,你現在可是我的搖錢樹,搖錢樹的事就是我的事,必須幫搖錢樹找回場子。」
我:「……」
我看了眼正前方已經黑了臉的美男,也就是上次不準江城擦邊的美男。不動聲色地點頭,又心黑地、親昵地拍了拍江城的手。
江城為什麼一定要自己單干,正是因為他將來隨時可能會為了眼前的美男,面對他家老爺子凍結他的銀行卡,把他趕出家門的窘迫困境。
不過,他現在要面對的是,已經走過來的黑臉美男。
我做完好事,深藏功與名,轉身走了。
翌日。
江城神色萎靡地出現在辦公室,打了個哈欠說:「月月姐,聽我說,謝謝你。」
我:「不客氣。」
他:「……」
他:「有你是我的福氣。」
17
轉眼,又一年冬。
我在一個深夜突然接到了謝澤的電話,他是用陌生號碼打的。
猝不及防聽到他的聲音,我蹙眉,正要掛了電話,他急急說:「靜月,我都想起來了。」
我:「哦,真晦氣。」
他:「……對不起。」
我:「不接受,不原諒。」
翌日,我從江城那里得知,謝澤公司一個項目砸了。即將面臨巨額賠款,賠不出來,他的公司可能會破產了。
難怪終于想起我來了。
這兩年,我忙著將公司做大,已經鮮少去關心謝澤的私事了。
偶爾閑下來休個幾天的假,回去公司江城就用幽怨的眼神看我。
妥妥是在控訴我擺爛,拖累他追求自由的速度了。
媽的,做老板做出了社畜的辛酸,誰懂!
只是 A 城這個不算小的城市,偶爾也有小的時候。
就半年前,我跟江城他倆出去吃飯,準備回家時,在地下停車場剛好撞見了林冉跟謝澤吵架。
因為謝澤疑似又綠了林冉。
就說出軌只有零次跟無數次的區別。
我看見兩人的時候,林冉正歇斯底里地跟謝澤吼:「謝澤,你他媽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原本都要走了,但看見兩人吵架,我停下了點火的手。
別問,問就是仇人過得不幸福,我垂死病中都能坐起來吃會兒瓜!
抬頭看去,謝澤不耐煩地吼了回去:「林冉,你是不是有病,那只是客戶,你能不能不要無理取鬧,你現在越來越像個不可理喻的神經病了。
ADVERTISEMENT
」
林冉不甘示弱:「誰見客戶一見就是一天,電話不接,信息不回。你若問心無愧,為什麼電話都不敢接。這不就跟當年你背著靜月,出來見我是一樣的嗎?」
我:「……」
敲你媽,別拿我鞭尸。
但不得不說,林冉不愧是情人上位的,這警惕心比我當年強多了。
我跟謝澤當年,我基本不過問他去哪里了。
兩人又爭執了一會兒,謝澤一把甩開林冉的手,上車,揚長而去。
獨留林冉一個人在停車場淚流滿面。
離得不遠,林冉轉頭準備去開車時,看見了我。
她愣了一下,狼狽地擦了把眼淚。
這形象,儼然就是個棄婦,離她當初來找我挑釁時的小白花形象,相差不是一星半點。
我朝她笑了笑:「嘖嘖,真愛。」
說完,也揚長而去。
謝澤到底有沒有綠了林冉,我不知道,我只要知道他們過得不好,就放心了。
我對他們現在只有一句話,尊重祝福,麻煩鎖死。
只是謝澤在公司出了問題后,突然又想起我跟他的過往,還深夜打電話給我。
他該不會是天真地以為,他一個電話我就能腦子不好地回去再跟他一起扛事兒吧。
咱就是說,他咋這麼會想。
別太荒謬!
但你別說,他可能真就這麼荒謬。
此后一個月,他給我打了無數次電話。
即使我一聽見他的聲音立馬就掛,拉黑了他幾個號碼,他也鍥而不舍地騷擾我。
打電話行不通后,還猥瑣地干起來了尾隨的勾當來惡心我。
這天,我加完班下班便見到了在公司外站著的謝澤。
胡子沒刮,煙頭落了一地,全身上下,就是大寫的兩個字:頹喪。
我懶得搭理他,徑直離開,卻被他抓住了手:「月月。」
他開口,我才聞到他身上的酒氣,嫌惡心地甩開他的手:「謝澤,你是有神經病嗎?我們都已經離婚兩年多了,你再來糾纏我有意思?」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